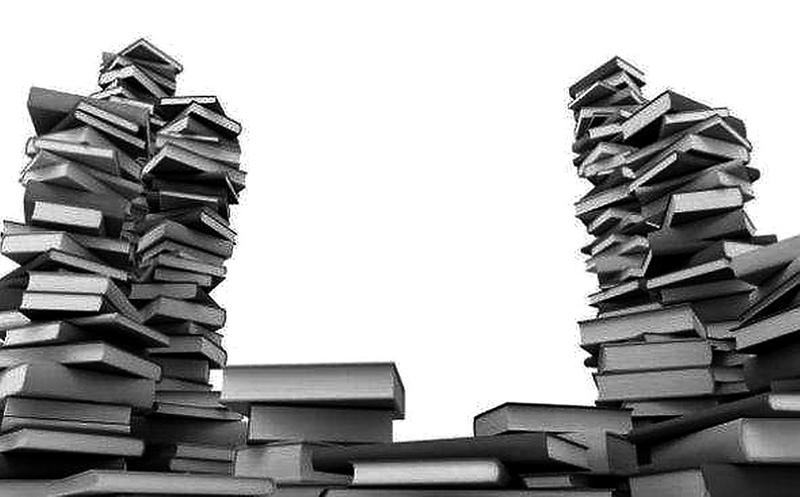
那是1983年吧,我還在上小學(xué)。村子里的朱姓人家的孩子考上了第四軍醫(yī)大學(xué),這個(gè)消息如長了翅膀似的,成為那個(gè)夏日村里最熱的話題。考上大學(xué),就從莊稼地里的泥腿子變成了吃皇糧的城里人,上學(xué)不花錢工作有安排,不用風(fēng)吹日曬,天天可以吃白米細(xì)面,這樣的人生之路是多少農(nóng)民子弟的夢想啊!
朱家又是敲鑼打鼓又是放炮擺席,不知眼紅了多少村人的眼睛。原本低眉順眼老實(shí)巴交的朱姓夫婦,不僅走路昂首挺胸咚咚有聲,就連說話都變得神氣起來,似乎唯恐有人不知道他家孩子考上大學(xué)的事。雖然有些人心里不服氣,但有啥辦法,誰叫人家孩子聰明,能百里挑一的考上大學(xué)呢?鄉(xiāng)親們一邊向老朱兩口子祝賀,贊揚(yáng)他教子有方,孩子聰明爭氣,一邊向他們討教孩子怎樣搞好學(xué)習(xí)、吃東西有什么講究。朱氏就很有經(jīng)驗(yàn)地告訴來取經(jīng)的人,孩子不能吃辣椒,也不能吃蒜,這些辛辣的東西,都會(huì)殺掉孩子的腦細(xì)胞,我們家孩子從來都不吃這些東西。母親聽說后,立即剝奪了我吃辣椒的權(quán)利。每當(dāng)我嘴饞偷吃這些東西時(shí),母親發(fā)現(xiàn)后就兇巴巴地吼道,還想不想上大學(xué)?還想不想變的聰明點(diǎn)?雖然,對(duì)于這些講究我半信半疑,但為了考上大學(xué),我還是聽從了母親的建議,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。
改革開放后,考大學(xué)是農(nóng)家子弟轉(zhuǎn)變身份的最好出路。為了考上大學(xué),有的學(xué)生甚至復(fù)讀多次,我的一位遠(yuǎn)房表哥就是這樣,他先后參加了四次高考,都因幾分之差與大學(xué)失之交臂。包工程有些積蓄的大伯最后和表哥商量道,要不咱上個(gè)自費(fèi)的大學(xué)吧?考的筋疲力盡的表哥最后無奈地接受了父親的建議。可是大學(xué)上了一個(gè)學(xué)期他就又跑回家,告訴大伯他還要去復(fù)讀。表哥說,雖然都是在一個(gè)學(xué)校學(xué)習(xí)。可是考上的學(xué)生每學(xué)期不用花學(xué)費(fèi),每月還有國家發(fā)的生活補(bǔ)助,而自己從學(xué)費(fèi)到生活費(fèi),都要掏腰包,明顯的矮人一等。再次復(fù)讀的表哥在第二年的高考中,終于考上了一所師范學(xué)校,最后當(dāng)了一名中學(xué)老師。
我是1998年參加的高考。“并軌”收費(fèi)自謀就業(yè)的機(jī)制,讓我懷著復(fù)雜的心情參加完高考的。大學(xué)畢業(yè)后,我先后在五家企業(yè)干過,但工作的不穩(wěn)定讓自己徹底失去了考上大學(xué)的榮耀。特別是當(dāng)自己每月的收入還不如沒上過大學(xué)做泥瓦工的堂哥收入高時(shí),自己上過大學(xué)的虛榮心徹底沒了。
不管世人如何評(píng)說,有競爭就有考試的規(guī)則,讓每一年的高考如期進(jìn)行著。對(duì)于每一年幾十萬的考生來說,也許無高考,不青春。